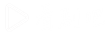每个牛马都从《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

电影是从九品小吏李善德陡然被封为「荔枝使」,接下了将荔枝从岭南转到长安这一棘手的任务开始的。
「荔枝使」有点像今天的快递员:快递送得及时就有奖励,超时了就要被平台罚单,在皇权时代就是杀头——古代与现代的牛马就这样奇异的地找到了共鸣。

《长安的荔枝》的原著作者马伯庸是一个非常擅长捕捉网络话题的作家,很难说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想的究竟是哪个时代。
比如李善德与胡商苏谅讨价还价那段,李善德估算需要七百六十六贯的成本,苏谅自愿给他追加三成,投资一千贯,李善德脱口而出「七百六十六贯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行文里突兀地跳出「九九六」三个字,打破「古」与「今」的界限,为小说平添了一分讽刺色彩。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抓住了原著中「以史喻今」的立意,导演大鹏延续了上一作《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把《长安的荔枝》拍成了一部职场喜剧——不,是职场综艺。
上司给李善德「画饼」的时候就真的拿出一个大饼;要展现打工人「摸鱼」就真的拿出一缸鱼;各部门「踢球」是就真的在踢球……这些综艺感十足的镜头语言尽可能地降低了代入门槛,加上演员动就面向镜头自白,主动打破「第四堵墙」,力图争取观众的最大共情。

除了是职场剧,《长安的荔枝》还是一部科幻电影。正式运输荔枝之前,李善德用纱眼格反复演算最佳路径就充满了科学实证的精神,与黄仁宇论断中那个「自古以来缺乏数目字管理」的中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如同纸上谈兵的赵括,马伯庸擅长用大量扎实可信的细节「诌」出一个主线天马行空的故事——《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小说往往是以古典时代为背景,动用极其庞大的资源来跨代解决技术问题。不同于「赛博朋克」或「蒸汽朋克」,科幻文学中或许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这一亚型,也许叫「牛马朋克」最为恰切。
「如果朝廷举倾国之力,不计人命与成本,转运速度一定可以再有突破」这句话就是整个故事的基石。「牛马朋克」的核心就是尽情地折腾牛马,让牛马创造出一切人间奇迹。

有趣的是,欧美科幻作家偶尔也写「牛马朋克」——比如特德·姜的《巴别塔》,但写得最生动的还是中国作家。马伯庸自不必说,《三体》第一部中秦始皇动用数以亿计的士兵排列成超级计算机以计算「三体」问题也是「牛马朋克」的妙笔。
这也不奇怪,马伯庸、刘慈欣都是从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目睹了整个中国经济加入世贸体系后火箭式的增长。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靠着土法大上快上,用蛮力破解技术难题,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这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但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这块土地上同样突出的现象。

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古老?什么是落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这些疑问不可能不折射在作家敏感的笔下。
从个人的角度看,《长安的荔枝》是一部职场喜剧片:敷衍塞责的同僚,盲目制定指标的上司,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拆台的体制……而从更宏大的角度看,《长安的荔枝》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科幻片,正是科幻般地把无数李善德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榨取到极致才缔造了大唐的「盛世」。
该如何面对这个由自己参与缔造,却完全与自己无关的「盛世」?

李善德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和近年来另一部广受好评的影片——《长安三万里》中的处理颇为不同。同样是以大唐盛世为背景,同样是一心在体制内受到重用,实现人生理想的主人公,《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有机会面见唐玄宗的时候却对塞外的见闻装聋作哑,而李善德在完成运送荔枝的任务后却和杨国忠算了一笔经济账,指责后者劳民伤财,几乎为此丧命。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三万里》中的另一位主角高适依然对朝廷充满热情,影片在高适击败吐蕃,成功保卫长安的激昂情绪中结束。《长安的荔枝》则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当已经被贬岭南的李善德闻知长安陷落、玄宗出逃的消息后只是怔怔地吃着荔枝,一边吃一边流泪,眼前闪过被焚成灰烬的长安街道。

其实比起小说版的结局,电影版的结局已经拔高了很多。至少电影版的李善德对大唐还是有感情的。原作小说的结局更具黑色幽默:知道玄宗失踪的消息后,李善德大吃特吃原本要当作贡品的荔枝,一口气吃了三十多个,直撑得病倒在床上。
家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说:「没有,没有,只是荔枝吃得实在太多啦。」主人公完全没有国破家亡的士大夫愁绪,皇帝倒台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饱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两者完全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因此他对所谓「国运」也是冷眼旁观。

据说《长安的荔枝》的灵感来自于马伯庸翻阅徽州文书时所发现的一个叫周德文的小吏。周文德本是安徽人,朱棣兴建北京时将他们强迁至北京安置。为了修建帝都,周德文负责筹办建筑材料,最后累死在任上,短暂的一生不过是史书上的聊聊数语。
马伯庸感慨:「汉武帝雄才大略,一挥手几十万汉军精骑出塞。要支撑这种规模的调动,负责后勤的基层官吏会忙成什么样。明成祖兴建北京、迁出金陵、疏通运河,可谓手笔豪迈,但仔细想想,这几项大工程背后,是多少个周德文在辛苦奔走……所以说,千古艰难唯做事, 一事功成万头秃。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可惜的是史书对这个层面,关注得实在不够多。」

马伯庸的人生经历了中国从落后的崛起的全过程,比较深刻地理解每一个增长的数字背后个体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比较不容易为整齐划一的宏大叙事所感动。
世纪之交的那批通俗文学作家很少能摆脱金庸的影响,马伯庸也不例外。金大侠的主人公往往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作结,《长安的荔枝》也属于这个序列上的作品。不过比起金庸后期的令狐冲、韦小宝,李善德就没有那样的洒脱。无言地大口吃供果吃到自己病倒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式的报复,带有几分自嘲甚至自虐的意味。

在港英时代的香港,金庸可以设想一个脱离了权力秩序的世外桃源作为大侠的归宿,但是对于新千年的作家来说,哪怕皇帝人间蒸发,权力仍是无远弗届的。
即使有种种腹诽,「牛马」的命运也不是与完全自外于权力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乐意或不乐意,「牛马」仍在某个层面上和权力绑定在一起,这种意识或许就是本世纪作家与上世纪最大的不同。